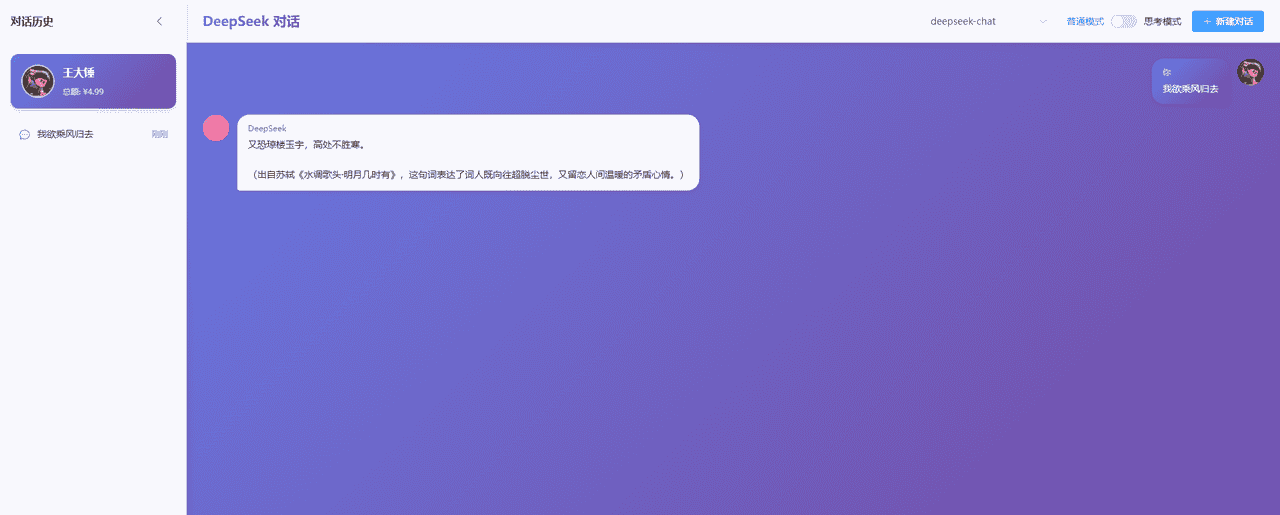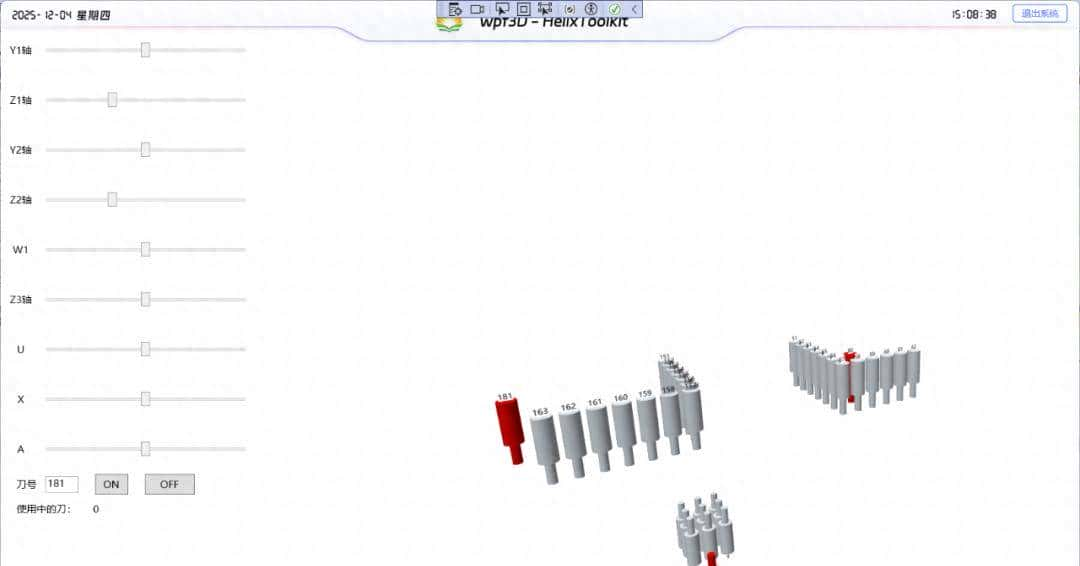第五章 公众无关紧要
个性化既是品牌区隔化过程的缘由,也是其结果。过滤泡如此吸引人,无非由于其满足了后物质主义放大的个人表达的欲求。不过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将我们的个性与内容流相匹配,这个过程就会侵蚀群体的共同经验。
新的个人信息环境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就是“非对称性”。“个体必须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大型的匿名机构[1],让陌生人来处理和使用,你看不见也不知道,而且常常后知后觉。”
个性化算法会导致身份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代码通过用户画像构建用户的媒体环境,而这一媒体环境有助于塑造用户未来的偏好。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但是至少程序可以精心设计一种优先思考“可证伪性”的算法,也就是说,着重于反证用户画像的算法。
旁人看得见我们眼中的事物[2],听得见我们耳闻的声响,正因有这些旁人的存在,我们才确知世界真的存在,你我是真有其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在美国,消除报纸影响[3]的唯一方法是增加报纸的数量,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我们一般认为,审查制度是政府改变实际和内容的过程。当互联网出现后,许多人希望它能彻底消除审查制度,但信息的洪流对政府来说太快太强了,无法控制。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依旧有可能操纵真相,只是做法不太一样:政府不是一味简单地彻底禁止某些词语或观点,而是越来越多地围绕二级审查——信息筛选、排版、导流和注意力控制。此外,由于过滤泡主要由少数几家公司聚焦控制,想针对个体来调整资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互联网早期的支持者曾经预测,互联网可以使权力去中心化,但在某些方面,互联网让权力更加聚焦了。
互联网早期的支持者曾经预测,互联网可以使权力去中心化,但在某些方面,互联网让权力更加聚焦了。
云端之主
为了了解个性化如何被用于政治目的,我访问了约翰·伦登(John Rendon)。
伦登和气地将自己描述为“信息战士和感知经理”。从位于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的伦登集团总部,他向数十家美国机构和外国政府提供服务。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攻进科威特城,电视转播画面是数百名科威特人快乐地挥舞着美国国旗。“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他后来问观众,“科威特人民被扣为人质长达七个月,生活水深火热,怎么能手持美国国旗?[4]而且还有其他联军国家的国旗呢?你们目前清楚了吧,那是我的工作之一。”
伦登大部分的工作是机密的,他等级很高,高级情报分析师有时也无法获得的信息,他都能接触到。他在乔治·W.布什时期对伊拉克进行的亲美宣传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不清楚。尽管有一些消息来源表明他是核心人物,但伦登否认参与其中。不过他的愿望很明确:伦登希望看到一个电视“推动决策进程”、“电子巡逻队取代边境巡逻队[5]”,政府“不战而胜”的世界。
所以,当他提到他的第一件武器是一本超级普通的同义辞典[6]时,我还是有点惊讶。伦登表明,改变公众舆论的关键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件事情。他描述了一个矩阵,一边是极端的语言或观点,另一边是温和的观点。通过情感分析就可以了解一个国民对某个事件的感受,列如对美国的新武器交易,伦登能找出正确的同义词,推动民意慢慢朝向“赞成”,“逐渐调整一场辩论的方向”。他说:“与其建构一个全新实际,接近现实并把它推向正确的方向,要容易得多。”
伦登和我曾出席过同一场研讨会,听我关于个性化主题的演讲。他告知我,过滤泡为感知管理提供了新方法。“第一步是从算法开始。你如果能找到一个办法,只让你的内容被算法跟踪、提取和呈现,就有更好的机会形塑信念。”实际上他暗示,我们如果找对地方,目前也许就能观察到民意随时间推移被算法慢慢挪动的迹象。
但如果过滤泡在未来可以轻易让伊拉克或巴拿马国家改变民意,那么伦登显然担心这种自我分类和个性化过滤也会对美国的民主造成影响。“如果我要对着一棵树拍照,”他说,“我有必要知道目前是什么季节。在不同季节,树木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快死了,或者只是在秋天掉叶子。”要做出好的决策,背景至关重大——这就是为什么军方如此关注他们所谓的“360度态势感知”。在过滤泡中,你看不到360度,可能连1度都看不见。
我把话题拉回用算法转移情绪这个问题上。“算法自我产生和自我强化信息流,那该怎么利用这个系统呢?我还得再思考一下,”伦登说,“但我认为我知道我会怎么做。”
“怎么做?”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咯咯笑了起来:“你有点奸诈。”他已经说得太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特·李普曼抨击政府的宣传运动。为了煽动民意参战,政府煞费苦心,逼迫全美数百家报纸加入统一战线,“让真相一步到位”。而目前的情况是,每个博主都是出版商,想让所有的博主“踢正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0年,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指出,互联网架空了中介机构和政府,赋予个人“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消费、分发和创建[7]自己的内容”的权力。
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视角。如果中介机构正在失去权力,那么该公司在一个大得多的剧本中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在线内容是通过少数几个网站传递给人们的,谷歌是其中最重大的一个。这些大公司代表着新的权力核心。虽然它们的跨国性使它们会抵制某些形式的监管,但它们也可以为那些寻求引导信息流的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
只要有数据库存在,国家就有可能访问它。这就是为什么支持拥枪权的积极分子常常以艾尔弗雷德·弗莱托(Alfred Flatow)为例。弗莱托是德国犹太人,奥运会体操选手。[8]1932年魏玛共和国日渐衰落时,他依法进行了枪支注册。1938年,德国警察敲开了他的门。他们事先翻遍了所有记录,准备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所以开始逮捕拥有手枪的犹太人。弗莱托于1942年在聚焦营被杀。
对全美步枪协会的会员们而言,这是关于国家枪支登记危险性的重大警示。与弗莱托类似的例子有成千上万,全美步枪协会数十年来不断宣传这些案例,成功地阻止了全国枪主资料库的建立。万一哪天法西斯反犹势力在美国掌权,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数据库找到拥枪的犹太人,但数量不会许多。
但全美步枪协会的关注点可能过于窄了一点。政府以外还有许多数据库,法西斯分子并不会认真遵循使用的法律条文。使用信用卡公司的数据或者基于安客诚追踪的数千种资料构建模型,可以超级准确地预测谁有枪支谁没有枪支。
即使你不是拥枪权的支持者,这个故事也值得关注。个性化的机制将权力转移到少数几个主要的公司行为体手中。海量数据的整合为政府(甚至是民主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
许多企业和初创企业目前不在内部存储网站和数据库,而是把资料存在外地,通过其他公司管理的大型服务器使用虚拟计算机运行。这些机器连接成网,计算能力强劲,存储空间无限,被称为云,它让客户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你如果有业务在云中运行,当处理需求扩大时,就不需要购买更多硬件,只需要租用更多的云即可。亚马逊的网络服务是这个领域的重大参与者之一,它拥有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网络服务器,无疑存储了无数的个人数据。一方面,云可以让地下室里的每个小创业家都能获得几乎无限的计算能力,快速扩展新的在线服务。另一方面,正如克莱夫·汤普森向我所指出的那样,云“实际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9]2010年,亚马逊迫于政治压力终止了激进网站“维基解密”的伺服器,该网站立即崩溃,无处可去[10]。
存储在云上的个人数据实际上比家庭电脑上的信息更容易被政府搜索到。联邦调查局需要法官的搜查令来搜查你的笔记本电脑。但是电子自由基金会(the Electronic Freedom Foundation)的一名律师说,你如果使用雅虎[11]、谷歌邮箱或Hotmail发邮件,就“会立即失去宪法保护[12]”。联邦调查局可以直接向该公司索取信息,不需要司法文书,也不需要上级许可,只要能事后辩称“事态紧急”就可以了。“警察会喜爱这个的[13],”隐私权倡导者罗伯特·格尔曼(Robert Gellman)在谈到云计算时说,“他们只要去一个地方,就能获取每个人的文件。”
由于数据的规模经济效应,云巨人们越来越强劲。但它们很容易被卷入法律纠纷,所以这些公司让政府开心的同时自己也能获益。2006年,司法部要求美国在线、雅虎和MSN提供数十亿份搜索记录,这三家公司很快就照办了[14]。(值得称赞的是,谷歌拒绝了这一要求。)咨询公司博斯艾伦汉密尔顿的信息技术专家斯蒂芬·阿诺德(Stephen Arnold)表明,谷歌的山景城总部曾有三名“某情报机构”的官员派驻。此外,谷歌和中情局共同投资一家名为“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的公司,该公司专注于通过数据关联性来预测现实中的未来事件[15]。
即使这种数据整合不会导致更多的政府监控,但这种整合本身就令人担忧。
新的个人信息环境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就是“非对称性”。“个体必须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大型的匿名机构,让陌生人来处理和使用,你看不见也不知道,而且常常后知后觉。”
新的个人信息环境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就是“非对称性”。乔纳森·齐特林在《互联网的未来及其挽救》(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and How to Stop It)一书中指出,“如今,个体必须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大型的匿名机构,让陌生人来处理和使用,你看不见也不知道,而且常常后知后觉”。
如果你住在小镇或一栋壁薄如纸的公寓楼里,我对你的了解和你对我的了解大致一样。这是社会契约的基础,在这份契约中,我们会刻意忽略一些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新的无隐私世界废除了这份契约。我可以在你浑然不觉的情况下知道你许多事情。搜索专家约翰·巴特尔告知我,“我们的行为中隐含着一笔交易[16],但我们还没算清这到底价值多少”。
如果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爵士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是正确的,隐私支持者维克托·迈耶—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写道,我们目前看到的无非就是“信息力量从无权者向有权者的再分配”。[17]我们知道彼此的一切,这是一回事,但如果集权实体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透彻,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那就是另一回事。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的不对称就是力量的不对称。
谷歌著名的座右铭“不作恶”据说是为了减轻外界对其的担忧。我曾经向一名谷歌搜索工程师解释说,虽然我不认为该公司目前是邪恶的,但如果它愿意,它似乎拥有做坏事所需的一切条件。他笑得很开心。“对,”他说,“我们不是邪恶的。我们用尽心力不做邪恶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想,伙计,我们绝对办得到!”
友善世界综合征
迄今为止,大多数政府和企业在相当谨慎地使用个人数据和个性化提供的新权力,但一些具有压迫性的政权明显是例外。即使抛开蓄意操纵不谈,过滤器的兴起也给民主国家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相当严重的后果。过滤泡让公共领域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话题和共同问题的讨论离个人越来越远。
第一,世界变得友善起来。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第一批开始思考媒体是如何影响民众政治思想的理论家,传播研究者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花了许多时间思考像《警界双雄》(Starsky and Hutch)这样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实则相当愚蠢,充斥着70年代警匪剧的陈词套路——浓密的小胡子,激昂的管弦配乐,简单化的善恶情节。这类的电视剧还有许多,一再翻拍的经典有《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檀岛警骑》(Hawaii Five-O),还有不怎么可能在21世纪再上演的《破茧飞龙》(The Rockford Files)、《特工克里斯蒂》(Get Christie Love)、《12号亚当》(Adam-12)等。
格布纳是一位二战退伍军人,后来成为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长。他超级严肃地对待这些节目。从1969年开始,他开始系统研究电视节目如何影响民众对世界的见解。实际证明,警匪剧效果显著。当电视观众被要求估计警察在成年劳动力中的占比时,相对于具有一样教育和人口背景的非电视观众来说,电视观众的估值会高许多。更令人不安的是,看过许多暴力电视节目的孩子,他们更可能害怕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暴力事件[18]。
格布纳称之为“无情世界综合征”(the mean world syndrome):如果你家每天看电视超过三个小时,而隔壁邻居家看得较少,那么实际上,与隔壁邻居相比,你在一个更无情的世界中长大,你的行为也会受影响。“你知道的,讲述故事的权力在谁手里[19],谁就能支配人的行为。”格布纳后来说。
格布纳于2005年去世,因此他有时间目睹互联网开始打破电视的垄断,信任他必定如释重负:尽管谁可以在线讲故事的权力依然相当聚焦,但互联网至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你如果想看地方新闻,但不想看地方台为了冲收视率而鼓吹犯罪恶化的消息,就大可以去看博客。
但“无情世界综合征”最多是形成了风险,一个新问题却即将出现:我们目前面临的可能是说服分析理论家迪安·埃克尔斯所说的“友善世界综合征”(a friendly world syndrome)[20],而其中一些最大和最重大的问题还未能引发我们关注。
愤世嫉俗的狗血情节促成了电视里的无情世界,但算法过滤产生的友善世界却可能不是故意的。根据脸书工程师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的说法,开发“点赞”按钮的团队最初思考了许多图形——从星号到竖起大拇指都有(但在伊朗和泰国,这是一个淫秽的手势)。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月里,这个按钮被称为“棒极了”,但脸书小组最终选择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赞”,[21]由于这个词全球通用。
脸书选择“赞”而不是“重大”,这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小设计:在脸书上,最受关注的故事是获“赞”最多的故事,而获“赞”最多的故事,会更受欢迎。
用过滤器产生无菌的友善世界,肯定不止脸书一家倾向于这么干。正如脸书顾问埃克尔斯向我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倾向于让用户自己调整筛选机制的推特,也有这种倾向。推特用户可以看到他们关注的人的大部分推文,但如果我的朋友和我不关注的人交流,他们的推文就不会出目前我的视野中。推特的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恶意,只是不想让我被不感兴趣的对话淹没。但结果是,我和朋友(思想和背景和我类似)间的对话比重太高,而那些可能让我接触到新思想的对话却被忽视了。
当然,能够穿透过滤泡并塑造我们对政治世界感觉的故事太多,不能用“友善”一词以蔽之。作为一个进步派政治新闻迷,我获取了许多关于萨拉·佩林(Sarah Palin)和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新闻。不过这些新闻的调性可想而知:人们转发它是为了用贝克和佩林的言辞来表达他们的沮丧,并与朋友们建立一种团结的感觉,这些朋友大致也有同感。我在动态新闻中看到的东西很少会动摇我的世界观。
比较容易在过滤泡中形成气候的是带有情绪的新闻。我在前文中谈过,沃顿商学院研究了《纽约时报》转发最多的热门新闻名单发现,那些能够激起强烈情绪——敬畏、焦虑、愤怒、幸福——的新闻报道更有可能被分享。如果电视给了我们一个“无情的世界”,那么过滤泡就给了我们一个“情绪世界”。
友善世界综合征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之一,是有些重大的公共议题会自动消失。很少有人会主动搜索和分享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信息。一般而言,枯燥、复杂、进展缓慢的问题——许多真正重大的问题都是这样——容易被挡在过滤泡之外。尽管我们过去常常依赖人类编辑来聚焦这些重大议题,但编辑们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正如环保组织Oceana发现的那样,即使利用广告也不必定能够唤醒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关注。2004年,Oceana发起一场运动,敦促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停止向海洋倾倒未经处理的污水,作为这项运动的一部分,它在谷歌上打出了广告:“协助我们保护全球海洋,一起加油!”但两天后谷歌撤下了广告,认为“其用语有抵制游轮行业[22]之意”,违反了谷歌关于品味的一般准则。显然,谷歌不欢迎用户在公共议题上用广告来影射企业。
在我们社会中存在重大、复杂却不愉快的议题,但过滤泡把它们阻挡在外,使它们隐形了。并且不仅是议题消失了,整个政治程序也逐渐消失于无形。
隐形的竞选
2000年,乔治·W.布什以远少于竞选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预期的票数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罗夫在佐治亚州的一些微瞄准媒体上启动了一系列实验,尝试通过查看广泛的消费者数据(“你更喜爱啤酒还是葡萄酒?”)来预测投票行为,判断什么样的选民更容易被说服,[23]什么样的选民更会被激励去投票。虽然实验结果仍未公开,但据说罗夫的发现大受共和党重点关注,成为其2002年和2004年成功的投票策略的核心。
左派也不甘示弱。凯特利(Catalist)是一家由几位前亚马逊工程师成立的公司,它建立了一个包含数亿名选民档案的数据库。任何组织和社团(包括MoveOn)都可以进行付费查询,协助决定该敲谁的门,向谁投广告。而这只是开始。民主党最提倡通过数据拉票的专家之一马克·施泰茨(Mark Steitz),最近在给进步派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精准宣传常常让人联想到轰炸——从飞机上投掷信息炸弹。但最好的数据工具可以协助我们根据观察到的人际沟通的情形,来与人进行接触,建立关系。如果派人去挨家挨户访问,发现某人对教育感兴趣,那么我们会带更多相关的资讯去找那个人和与之类似的人。亚马逊的推荐引擎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24]现今的趋势很明显:我们的策略重点正从摇摆州转向单个的摇摆人。
试想目前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各派争相来拉票。
会不会找你?这取决于你是谁,真的。如果数据显示你常常投票,并且你过去可能是摇摆不定的选民,那么这场拉票战可能会争得不可开交。你会被广告、电话和朋友的邀请轮番轰炸。你如果不是有票必投,那么会受到各种激励去投票。
假设你更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你一般只给一个党的候选人投票。对于另一阵营的数据处理专家来说,你看起来不是特别会被说服。而由于你常常在总统选举中投票,你自己的党也不会打电话催你。你投票只是尽公民义务,实则你对政治并不那么感兴趣。相比而言,你对足球、机器人、癌症治疗以及你居住的城镇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那么您的个性化新闻订阅就会反映出这些兴趣爱好,而不是呈现最近一次的竞选活动新闻。
在一个被过滤的世界里,候选人专门瞄准那些易于被说服的小众,而你会知道竞选都发生了些什么吗?
即使你浏览到一个为普通选民报道比赛的网站,也很难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场选举的议题是什么?你看不到以全民为诉求对象、涵盖所有人政见的信息,由于候选人针对的不是普通公众。相反,候选人会设计一系列碎片化的政见,用以攻破中间选民的个性化过滤器。
谷歌正在为这样的未来做准备。早在2010年,它就已经为政治广告配备了24小时“战情室”[25],即使是在临近投票前的10月的凌晨,也能快速审核通过并激活新广告。雅虎正在进行一系列实验,一边是各选区公开的曾经投票的名单,一边是自家网站上采集到的点击信号和网站历史数据,看看能否将两者匹配起来。旧金山一家叫“拉普里夫”(Rapleaf)的数据聚合公司,正尝试将脸书的社交图谱信息同投票行为联系起来——这样它就可以根据你朋友的反应向你展示最适合你的政治广告。
想和选民谈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这种冲动并不坏——这肯定比一提到“政治”一词,许多人就目光呆滞要好太多。互联网的确 释放了整个新一代活动家的协调能量,目前想要找到在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但是,虽然容易把这些人集结成群,不过随着个性化的发展,任何特定群体想要接触更为广泛的受众将变得更加困难。在某些方面,个性化对公共生活本身构成了威胁。
由于政治广告的艺术水平比商业广告落后了五年,因此个性化导致的变局还在不断发展。但第一,“过滤泡政治”可以让更多人只针对单一问题去投票。和个性化媒体类似,个性化广告是一条双向道:由于我开的是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所以我可能会看到一则关于环保的广告,而这则广告让我更加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如果某个国会竞选团队能够确认,这是最有可能说服我的议题,那干吗还要费心告知我其他所有问题呢?
从理论上讲,市场因素将继续鼓励候选人接触非投票者。但另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允许用户删除他们不喜爱的广告。毕竟对脸书和谷歌来说,如果让用户看到不喜爱的想法或服务则是一种失败。由于人们倾向于排斥与个人理念相左的广告,那么被说服的可能性就更小。“如果必定数量排斥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共和党人看到米特的广告,并点击‘攻击’,”共和党政治顾问文森特·哈里斯(Vincent Harris)写道,“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所有米特·罗姆尼的广告被封杀。不管罗姆尼的竞选团队想在脸书上砸多少钱,[26]都无济于事。”迫使候选人想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许会催生更有想法的广告,但这也可能会使广告预算飙升,让竞选活动变成砸钱游戏。
过滤泡带来的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它使得公共辩论变得越来越困难。
过滤泡带来的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它使得公共辩论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竞选广告的细分类别和信息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难追踪是谁在对谁说什么。相比而言,电视是比较容易监看的——你可以在每个有线电视区录下对手的广告。但如果对方的选民群体很有针对性,年龄在28岁到34岁之间,在脸书页面上自曝是U2乐队的粉丝,曾捐款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竞选,并且是白人犹太人,那么竞选团队又该怎么办呢?
2010年,保守派政治团体“美国就业保障”(Americans for Job Security)在电视上发布广告,错误地指责国会众议员皮特·胡克斯特拉(Pete Hoekstra)拒绝签署一项无新税保证书。胡克斯特拉向电视台展示了签署的承诺,叫停了广告[27]。仲裁真相的大权被电视台老板一手包揽,这并不好——我自己也花了相当多时间和他们争论——但有总比没有好。目前还不清楚,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是否有资源或兴趣在接下来的选举周期中,在登载的数十万个不同广告中充当真实性的仲裁者。
随着个性化的政治广告增加,不仅每个阵营回应对手、核查对手言论真实性的难度越来越大,记者们面临的挑战也在升级。在未来,记者和博主可能无法轻易接触到最重大的广告,想把记者排除在精准广告之外易如反掌,而记者却很难编造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摇摆选民的形象。(解决这个问题的简易方法是,要求竞选团队立即公布所有在线广告的内容和每个广告的目标对象。现阶段,即时公布广告内容是零零散散的,而目标受众则属于机密。)
这并不等于说,电视上的政治广告有多棒。大多数情况下,电视政治广告尖锐、刺眼又不讨喜。如果可以,大多数人则会把它们拒之门外。但在大众传播时代,电视政治广告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提醒人们选举将至;第二,协助人们认识候选人的价值观、政见、论点,这些都是政治辩论的要点;第三,为公众对话奠定基础,方便大家辩论眼前的政治决策——类似于你在超市排队时的闲聊。
尽管有种种缺点,但选举运动依旧是辩论国家大事的主要场合之一。美国要纵容酷刑吗?我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还是支持社会福利的国家?谁是我们的英雄,谁是恶棍?在大众传播时代,选举运动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些功能可能维持不了太久了。
区隔化
在《大群体》(The Big Sort)一书中,消费趋势专家沃克·史密斯(J.Walker Smith)告知作者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现代政治营销的目标就是“提高客户忠诚度——用市场营销的术语来说就是提高平均交易规模,或者就是增加注册的共和党人投票给共和党的可能性[28]。这是一种应用于政治上的商业哲学,我认为这很危险,由于这样做的出发点不是尝试形成共识,不是让人们向全民利益的方向思考”。
但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开始走这条路,这与过滤泡崛起的缘由一样:个性化让选举的预算都花在了刀刃上。这也是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思考什么对自己重大的自然结果。当人们不必担心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时,他们就更关心那些代表他们的产品和领导人是否具有个性。
罗恩·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教授称这种趋势为“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他认为后物质主义有一个基本前提,“人们把最看重的主观价值放在最短缺的事物上”。在一项跨越了80个国家、历时40年的调查中,英格哈特发现,那些从来不用担心自己温饱问题的人,其行为方式与出身贫寒的父母截然不同。英格哈特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中写道:“我们甚至可以明确地指出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哪些议题最能在政治上得到回应[29]。正确率远胜于随机。”
虽然国与国之间观念差异显著,但后物质主义者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点:他们对权威和传统制度不那么尊重,威权主义政治铁腕人物的吸引力似乎与对生存的基本恐惧有关;他们更能容忍差异性,一张引人注目的图表显示,生活满意度越高的人对邻居是否是同性恋的宽容度也越高。前几代人重点关注财富和秩序,但后物质主义者则重点关注自我表达和“做你自己”。
有点令人困惑的是,后物质主义并不意味着反消费。实际上后物质主义正是我们当前消费文化的基石:前人购买东西,是由于需要物品来维系生存,而目前购物则是为了自我表达。同样的动力也适用于政治选举,选民越来越多地根据候选人是否代表了自己的志向来评价他们。
结果就是营销人员所谓的品牌区隔。过去,品牌主要是为了强调产品质量——“多芬香皂品质纯净,由最上等的原料精制而成”——广告更注重推销基本价值。但目前,品牌开始成为表达身份的媒介,它需要与不同群体的人们更加密切地交流。不同的群体想要表达不同的身份诉求,结果品牌开始分化。想要更好地理解巴拉克·奥巴马所面临的挑战,理解蓝带啤酒是个好方法。
千禧年初,蓝带啤酒陷入财务困境。蓝带的核心客户群是乡下白人,但这个群体的消费市场已经饱和。1970年蓝带的销售业绩是2000万桶,如今每年销量还不到100万桶。蓝带如果想卖更多的啤酒,就必须另外开辟市场。中层营销经理尼尔·斯图尔特(Neal Stewart)正是这样做的。他发现蓝带在俄勒冈州的小镇波特兰销售强劲,而当地流行一种带有讽刺意味地怀念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还记得卡车司机的帽子吗?)。斯图尔特想,蓝带既然无法让消费者真诚地畅饮,也许可以让人们自嘲地喝下。蓝带开始赞助潮人活动[30]——画廊开幕式、自行车快递员比赛、滑板比赛等。不到一年,蓝带的销售业绩大幅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如果你走进布鲁克林住宅区的一家酒吧,蓝带比其他低端美国啤酒更容易买到。
这不是蓝带走过的唯一的创新改造之路。在中国,蓝带被誉为“中外驰名的名酒”,已经跻身大都会精英阶层的奢侈饮料行列。蓝带的广告将其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相提并论,将其倒在香槟杯中,放在木桶顶部,一瓶售价约44美元[31]。
蓝带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典型的品牌重塑,而是被“重新定位”以吸引另外一个群体。白人工人阶级中许多人依旧真诚地喝着蓝带啤酒,这是对本地文化坚实的肯定。都市潮人喝蓝带啤酒,则是调皮地眨眨眼再喝。富裕的中国雅皮士把它作为香槟的替代品和炫耀性消费的象征。同一种饮料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细分市场的离心力拉动下,每个不同的市场都想要代表其身份的产品。政治领导权也和蓝带品牌一样发生分裂。巴拉克·奥巴马变色龙式的政治风格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我是一个空白的屏幕[32],”他在2006年出版的《勇往直前》(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写道,“让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在上面表达自我的主张。”奥巴马个人的政治取向原本就多元,但在这个区隔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优势。
(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也可以促进整合,根据《赫芬顿邮报》的报道,奥巴马对旧金山的捐款人说,部分民众“执着于枪支与宗教”,这一评论成为竞选对手反对他的热议话题。而同时,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的潮人如果读对了博客,则可以了解到蓝带啤酒在中国的营销策略。虽然区隔化行销的招数被曝光,区隔化的手段危机重重,还削弱了自身的诚信,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事态,只会促使其更加奋力去调整目标。)
个性化既是品牌区隔化过程的缘由,也是其结果。过滤泡如此吸引人,无非由于其满足了后物质主义放大的个人表达的欲求。不过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将我们的个性与内容流相匹配,这个过程就会侵蚀群体的共同经验,导致政治领导力濒临崩溃。
正如奥巴马所学到的,这种区隔化的不利之处在于,做领导人更加困难了。在不同政治选区采取不同的言行并不新鲜,实际上这可能和政治活动本身一样古老。但政治人物总有言行是重叠的,要面对所有选区,而这样的言行正在大幅减少。你可以代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也可以代表某些东西,但同时做两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
个性化既是品牌区隔化过程的缘由,也是其结果。过滤泡如此吸引人,无非由于其满足了后物质主义放大的个人表达的欲求。不过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将我们的个性与内容流相匹配,这个过程就会侵蚀群体的共同经验,导致政治领导力濒临崩溃。
话语与民主
对于后物质主义政治而言,好消息是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公民可能会变得更加宽容,更喜爱自我表达。但是它也有黑暗的一面。英格哈特的学生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专注于环境运动中的后物质主义研究,他告知我,“后物质主义的阴影是自我卷入太深……目前之所以能够享受优质生活,全靠群体的努力,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些是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33]”。在后物质主义世界里,你的终极任务就是自我表达,但支持这种表达的公共基础设施却不存在了。不过,我们可能找不到公共问题,但公共问题会找到我们。
我的家乡缅因州林肯维尔住着900人,那里每年会举行几次市民大会。这是我对民主的第一印象:数百名居民挤进小学礼堂或地下室,讨论学校扩建、道路限速、土地划分和狩猎禁令等。在一排排灰色金属折叠椅当中的过道里,有一个小讲台和一个麦克风,人们可以排队等待发言。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有些发言者喋喋不休,有些人会被轰下台。但它给了我们所有人一种是我们构成了这个社区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如果讨论是关于鼓励更多的沿海地区贸易的议题,你就会听到富裕的避暑度假者为享受平静安宁提出抗议,带着抵制发展情绪的嬉皮士主张要回到自然,而世代住在海边乡下的低收入家庭则希望地价赶快涨起来。这些观点你来我往,有时接近共识,有时分裂论战,但一般会引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决定。
我一直喜爱那些市民大会的运作方式。但直到我读了《全民对话》(On Dialogue),我才完全理解他们的成就。
戴维·博姆(David Bohm)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雷,是匈牙利和立陶宛犹太人的后裔,家中经营家具店,出身寒微。他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很快就和一小群理论物理学家打成一片,并接受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指导,后者与各国竞争制造原子弹。他在1992年10月去世,享年72岁,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博姆的本行是量子数学,但他投入了大量心血研究先进文明产生的问题,尤其是核战的可能性。“技术以越来越大的力量继续前进,是福是祸?”他写道,“这些问题的源头是什么?我认为,基本源头是思想[34]。”对博姆来说,解决办法很清楚,那就是对话。1996年,他撰写了一本关于对话的权威著作。
博姆写道,“交流”,字面上的意思是让事情变得具有共通性。虽然有时候,这种变得具有共通性的过程仅仅涉及与一群人共享一些资料,但更常见的方法是让这群人聚集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共同的意义。“在对话中,”他写道,“人们都是共享共同意义的参与者[35]。”
博姆并非第一个看到对话具有民主潜能的理论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媒体理论也有类似的观点。对这两者而言,对话是特别的,由于它为一群人提供了一种经由民主创造文化、形成观念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运作依赖对话。
博姆也看到了对话的另一种用途: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了解复杂系统全貌的方式,甚至是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的部分。博姆说,人的倾向是分割想法和对话,使其碎片成为与整体无关的片段。他以一块摔碎的手表为例:与之前组成手表的零件不同,被摔碎的零件与手表整体没有关系,它们只是支离破碎的玻璃和金属。
正因这种品质,林肯维尔的市民大会才显得特别。即使群组不能总是就未来的方向达成一致,这个过程也有助于描绘一张共享的地图。每个零件都了解我们同整体的关系何在,这反过来又推动民主治理成为可能。
一个被算法分类和操纵的公共领域,本质上是零碎的,并且排斥对话。
市民大会还有另一个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在碰到突发情况时随机应变。在社交图谱的研究领域,对社区的定义是一组紧密相连的节点——我的朋友不仅认识我,彼此之间也有独立的关系,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社区。沟通可以建立更强健的社区。
最终,只有公民能够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去思考,民主才会起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的见解。我们需要接触其他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但过滤泡却把我们推向反方向,它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狭隘的私利就是一切。虽然这有利于网上购物,但不利于众人一起改善决策。
约翰·杜威写道,民主的“首要困难”是发现分散的、流动的和多种多样的公众如何认识自己,从而定义和表达自己的利益[36]的方式。在互联网发展初期,许多人对新媒体抱有这样的远大愿景:它最终将提供一个媒介,让整个城镇甚至全国通过对话共同创造文化。但个性化给了我们一些超级不同的东西:一个被算法分类和操纵的公共领域,本质上是零碎的,并且排斥对话。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设计系统的工程师要这样编写算法?
注释:
[1]Jonathan Zittrai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and How to Stop I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1.
[2]Hannah Arendt,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New York: Penguin, 2000), 199.
[3]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001).
[4]Laura Miller and Sheldon Rampton, “The Pentagon's Information Warrior: Rendon to the Rescue, “PR Watch 8, no.4(2001).
[5]John Rendon, as quoted in Franklin Foer, “Flacks Americana, “New Republic, May 20, 2002, accessed Feb.9, 2011, www.tnr.com/article/politics/flacks-americana?page=0, 2.
[6]John Rendon, phone interview by Author, Nov.1, 2010.
[7]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 “The Digital Disrup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Dec.2010.
[8]Stephen P.Halbrook, “'Arms in the Hands of Jews Are a Danger to Public Safety': Nazism, Firearm Registration, and the Night of the Broken Glass, “St.Thomas Law Review 21(2009): 109-41, 110, www.stephenhalbrook.com/law_review_articles/Halbrook_macro_final_3_29.pdf.
[9]Clive Thomps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Brooklyn, NY, Aug.13, 2010.
[10]Peter Svensson, “WikiLeaks Down? Cables Go Offline After Site Switches Servers, “Huffington Post, Dec.1, 2010, accessed Feb.9, 2011, 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2/01/wikileaks-down-cables-go-_n_790589.html.
[11]尽管雅虎的官方标识是Yahoo!, 但为方便阅读起见, 我在全书省去了感叹号。
[12]Christopher Ketcham and Travis Kelly, “The More You Use Google, the More Google Knows About You, “AlterNet, Apr.9, 2010, accessed Dec.17, 2010, www.alternet.org/investigations/146398/total_information_awareness: _the_more_you_use_google, _the_more_google_knows_about_you_?page=entire.
[13]”Does Cloud Computing Mean More Risks to Privacy?, “New York Times, Feb.23, 2009, accessed Feb 8, 2011, http: //bits.blogs.nytimes.com/2009/02/23/does-cloud-computing-mean-more-risks-to-privacy.
[14]Antone Gonsalves, “Yahoo, MSN, AOL Gave Search Data to Bush Administration Lawyers, “Information Week, Jan.19, 2006, accessed Feb.9, 2011, 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ecurity/government/showArticle.jhtml?articleID=177102061.
[15]Ketcham and Kelly, “The More You Use Google.”
[16]John Battelle, 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12, 2010.
[17]Viktor Mayer-Scho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7.
[18]George Gerbner, “TV Is Too Violent Even Without Executions, “USA Today, June 16, 1994, 12A, accessed Feb.9, 2011 through LexisNexis.
[19]”Fighting 'Mean World Syndrome, '”GeekMom Blog, Wired, Jan.27, 2011, accessed Feb.9, 2011, http: //www.wired.com/geekdad/2011/01/fighting-%E2%80%9Cmean-world-syndrome%E2%80%9D/.
[20]Dean Eckles, “The 'Friendly World Syndrome' Induced by Simple Filtering Rules, “Ready-to-Hand: Dean Eckles on People, Technology, and Inference Blog, Nov.10, 2010, accessed Feb.9, 2011, www.deaneckles.com/blog/386_the-friendly-world-syndrome-induced-by-simple-filtering-rules/.
[21]”What's the History of the Awesome Button ( That Eventually Became the Like Button) on Facebook?”Quora Forum, accessed Dec.17, 2010, www.quora.com/Facebook-company/Whats-the-history-of-the-Awesome-Button-that-eventually-became-the-Like-button-on-Facebook.
[22]Hollis Thomases, “Google Drops Anti-Cruise Line Ads from AdWords, “Web Advantage, Feb.13, 2004, accessed Dec.17, 2010, www.webadvantage.net/webadblog/google-drops-anti-cruise-line-ads-from-adwords-338.
[23]”How Rove Targeted the Republican Vote, “Frontline, accessed Feb.8, 2011, 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architect/rove/metrics.html.
[24]Mark Steitz and Laura Quinn, “An Introduction to Microtargeting in Politics, “accessed Dec.17, 2010, www.docstoc.com/docs/43575201/An-Introduction-to-Microtargeting-in-Politics.
[25]”Google's War Room for the Home Stretch of Campaign 2010, “e.politics, Sept.24, 2010, accessed Feb.9, 2011, www.epolitics.com/2010/09/24/googles-war-room-for-the-home-stretch-of-campaign-2010/.
[26]Vincent R.Harris, “Facebook's Advertising Fluke, “TechRepublican, Dec.21, 2010, accessed Feb.9, 2011, http: //techrepublican.com/free-tagging/vincent-harris.
[27]Monica Scott, “Three TV Stations Pull 'Demonstrably False' Ad Attacking Pete Hoekstra, “Grand Rapids Press, May 28, 2010, accessed Dec.17, 2010, www.mlive.com/politics/index.ssf/2010/05/three_tv_stations_pull_demonst.html.
[28]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8), 195.
[29]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30]Neal Stewart, “Marketing with a Whisper, “Fast Company, January 11, 2003, accessed January 30, 2011, www.fastcompany.com/fast50_04/winners/stewart.html.
[31]Max Read, “Pabst Blue Ribbon Will Run You $44 a Bottle in China, “Gawker, July 21, 2010, accessed Feb.9, 2011, http: //m.gawker.com/5592399/pabst-blue-ribbon-will-run-you-44-a-bottle-in-china.
[32]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 Crown, 2006), 11.
[33]Ted Nordhaus, 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Aug.31, 2010.
[34]David Bohm, Thought as a System(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
[35]David Bohm, On Dialogue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6), x-xi.
[36]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Athens, OH: Swallow Press, 1927), 146.
相关文章